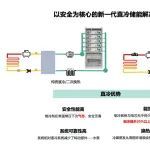太阳石丨父亲挑煤泥
天刚蒙蒙亮,父亲便起床准备扁担和畚箕。见父亲已经坐起,母亲在黑暗中摸索着把煤油灯点亮,顺手披件衣服,打着哈欠去为父亲做早饭。趁着父亲吃早饭的工夫,母亲为他准备换洗衣物。一切安排妥当后,父亲把畚箕和扁担捆在自行车后座上,又把打包好的衣物往车把上一挂,借着晨光赶往县氮肥厂。
县氮肥厂的大烟囱后面是一堵高墙,高墙下面有三根粗钢管——那钢管粗得并排钻进两个成年人还绰绰有余。氮肥厂排出的废水通过这些钢管流入墙外一排巨大的蓄水池。蓄水池中沉淀下来如粉状的“黑土”就是煤泥。那个时候,我们习惯称之为“水煤炭”。父亲和工友们要及时把这些煤泥从蓄水池里挖出来,装上大货车,运去回收工厂。
沥去水的煤泥黑黝黝的,表面平坦,像一块巨大的墨饼,踩上去却如同陷入一片黑色的沼泽地。我曾试着在上面站立过一次,没一会儿,脚就越陷越深。当我手忙脚乱地把脚连着雨靴费力拔出来时,传来“咕唧”一声响,还带出长长的泥丝。等完全离开那片“黑泥海”,我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。在这样的煤泥里行走一步都困难,更别说劳作了。
可生活的压力不给父亲选择的机会,我见过父亲挑煤泥,那是我至今都不会忘记的画面。刚开始时,父亲和工友们站在池边上,把最靠边的煤泥挖出来挑走。这些煤泥靠近池边,含水量少,比较好铲。等挖完池边的煤泥后,就开始挖蓄水池中心的煤泥。这部分是最难挖出来的。
煤泥被装入畚箕后,看起来不多,实际上特别重。父亲把扁担压在肩膀上试了试,找到平衡点后,弯下腰,咬紧后槽牙,费力地把一担煤泥挑起来。又湿又重的煤泥压得父亲龇牙咧嘴,双腿不停颤抖。可父亲并没有把煤泥放下,而是稍作停顿后,把肩膀上的扁担挪了挪,才挑着这百斤重的煤泥,颤颤巍巍地走出这片黑色的煤池,送到停在蓄水池边的货车上。几趟下来,父亲的衣服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,后背也早已湿透。可父亲从未喊过一声苦,就像老黄牛一样,只顾着挑起这副重担,默默劳作。
休息间隙,父亲把衣服脱下来顺手一拧,汗水夹杂着煤泥“哗啦啦”地落在水泥地上,溅起的细碎泥星子密密麻麻沾满了他的裤脚,而他那磨出茧子的肩膀上红肿一片。父亲往肩上抹点红花油,坐在简易工棚的屋檐下默默地抽着烟,等待蓄水池再次被煤泥灌满。
多少年来,父亲挑煤泥的画面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,那样清晰,让我的心隐隐作痛。不善言辞的父亲挑起的何止是一担煤泥,那是生活的艰辛和对家庭的责任。现在,我也做了父亲,也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。虽然日子不再像当年那样捉襟见肘,但也上有进入人生暮年的老人,下有刚步入青春期的儿子。每当生活的压力如山一般倾倒过来时,我对父亲的理解也愈发深刻。
一根扁担、一担煤泥,压弯的是父亲的脊梁,撑起的却是全家的天。父亲老了,背早已佝偻,那沾了不知多少煤泥的畚箕也不知所踪。但他挑起煤泥一声不吭往前赶的背影,一直都印在我的脑海里,指引着我一步步踏实向前走去。
作者:肖日东 版面编辑:袁理
来源:中国煤炭报
声明:本文系转载自互联网,请读者仅作参考,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若对该稿件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质疑,请立即与铁甲网联系,本网将迅速给您回应并做处理,再次感谢您的阅读与关注。
不想错过新鲜资讯?
微信"扫一扫"